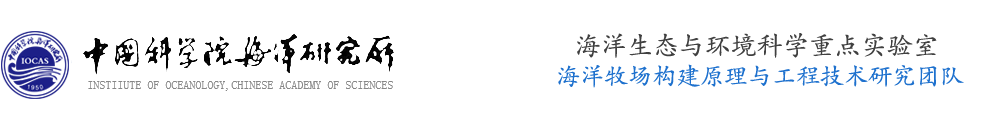实验室文化
联系我们
地 址:青岛市南海路7号
电 话:--
邮 箱:--
电 话:--
邮 箱:--
作品精选
当前位置:
首页 > 新闻中心 > 作品精选
兄弟,珍重
发布时间:2017/5/18 来源:沙噀 阅读:1036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第一次来到青岛,看到了海,亲口尝了海水的苦涩,更为重要的是我确定了自己奋斗的第一个目标——攻读博士学位。
导师要求极严格,刚报到就指派我和其他三位同门到东营去扎围隔,开展鱼虾贝混养实验。孔兄,是我结识的一位兄弟,他是来自曲阜的农民工,年方二十四岁,小我五岁,中等身材,面色黝黑,干练聪明。为了娶媳妇,来到东营养虾挣钱。公司急需解决对虾大规模死亡问题,很支持我们的工作,安排孔兄帮我们做实验。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扎围隔,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工程。先是购买木头和围隔布,就颇费周折。木头是松木,需要修整。我们不知道松木皮脱落时,会形成一些小刺,结果两个师妹每人都扎了十几处。我们拿出导师设计的图纸,提出了相关要求,孔兄就开始我们一起琢磨了,又在地上划来划去,最后确定了实施方案、通知公司派人,公司调动了一百多号民工,我们和孔兄一同指挥,四十多个围隔很快就扎起来了。从此,我对孔兄刮目相看,一个农民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比我差,甚至比我还强。
导师选择了罗非鱼作为滤食性动物,解决池塘有机物过剩问题,这下子倒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好麻烦。罗非鱼起源于海水,后来生活在淡水,可以忍受正常的海水盐度,但需要驯化。没想到驯化罗非鱼如此不顺利,第一次我们从青岛运回罗非鱼,到公司里驯化,孔兄和我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,遗憾的是这批鱼还没有达到盐度30时就开始大批死亡了。究其原因,应该是捕捞运输过程受伤所致。第二次我们终于将鱼驯化到盐度30,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鱼一条条量体长、称体重,在逐个放入围隔。第二天信心满满的巡塘。说句实在话,我当时死的心都有,放入的实验鱼大多飘在围隔的水面上。第三次运鱼、驯化鱼更为小心,孔兄建议带水称鱼,放了鱼再称水和桶。第二天巡塘,孔兄坚决不要我和他一起去,我想他怕我看到结果不好而受不了。他去巡塘了,我在低矮的办公室里苦等,满屋的苍蝇嗡嗡叫,让我心烦意乱。大约一个小时过后,他回来告诉我情况不错,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。中午吃饭时,他拿出笔记本,逐一告诉我哪几号池需要补多大的鱼,事实上还是死亡了一些。
实验终于安排妥当,孔兄每天帮我划船、测水温、溶氧、pH和透明度等,每月全面监测一次围隔水质等等。有时我不在现场,孔兄也照样进行,不折不扣。春去秋来,实验结束了,混养的鱼和贝成活和生长都很好,遗憾是虾一个也没有活。我身心疲惫,临行前和孔兄喝了点酒,期间孔兄说了很多我该说的感激的话。他说这段时间他学到很多东西,希望将来还和我一起干,尽管没有赚到钱。依依惜别,我回到青岛。后来,孔兄给我写了一封信,问我要不要他来青岛干活,我当时只是一名学生,哪能决定,只好婉拒了。若干年后想起这位仁兄,但没有找到唯一的那封信,联系地址记不住了,从此也就杳无音信了。
第二年,我们来到海阳继续开展围隔实验,我知道这是我攻读博士期间十分重要的一年,成败与否将决定我是否能按时拿到学位和未来发展方向。到了公司,老总安排见他们的技术总管于兄,也就是我结识第二位兄弟。于兄年长我五岁,是当地的“高材生”和“明白人”。他个人不高且偏瘦,倒像是江南才子,而不是山东大汉。也许是文人相轻,一开始,于兄对我们的实验并不感兴趣,我估计是他认为我们干的活与他们需要的相差甚远。他一天到晚都拿着书看,很少和我们说话,大约一个月过后,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。原因在于他发现我们干活比他们更认真、更能吃苦,这一点可能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。说起来实在有趣,我请于兄帮忙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鸡粪。“养鱼先养水”,按照导师的设计,我要将开展有机肥在调控水质过程中的作用。于兄问清缘由,十分热情打电话派车,找晒场。鸡粪实在很臭,于兄和我们一起卸车,一起晾晒。又派人拿来稻草和雨布,以备大风大雨等不测。更为甚者,他专门安排一个偏僻的储藏室保存鸡粪,以后的几年里,我们团队一直使用这同一批鸡粪做实验。
在此期间,我的爱人和女儿到现场来看我。于兄安排嫂子借了一家新房,打扫得干干净净,包括蚊帐铺盖,锅碗瓢勺,一应俱全。更有意思的是几家邻居大嫂送来了鸡蛋、茄子、土豆等,每样都是六个,估计是图个吉利吧。爱人和女儿走后,我为了感谢于兄和嫂子,买了一瓶白酒,请嫂子炒了两个菜,兄弟俩平分了白酒,结果于兄喝高了,吐得一塌糊涂,连嫂子也埋怨我了。回想起来,实在对不住于兄了。一年多的实验结束了,我回到了青岛,如愿按期获得了博士学位。本想请于兄和嫂子来青岛转转,他说“还是你来海阳吧,我们进城就转向、迷糊”。
第三位兄弟其实是我的师弟,晚我一年入师门,但我在他面前一直没有敢称师兄。因为当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,也就是说到了博士研究生报考年龄的极限值了,尤为重要的是他已经某大学的副教授了,学问钢钢的,还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文。于是,我称呼他王老师,他叫我老杨。他那年来攻读博士学位确实让业界不少同仁吃了一惊,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的宝贝女儿也是那年上大学,可谓双喜临门吧。这位王兄也是有于兄同样的毛病,文人相轻呗,但他玩得更深沉,毕竟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,都有自己看人、评价人的独到之处。王兄真正和我开始交心是一次抓虾之后。事情是这样的,围隔做好以后,需要大量的虾苗投放,此时的虾苗都在大池里,拖网抓怕伤害了虾苗,又怕发生应激反应,导致虾苗发病。当时虾苗基本上都是携带病毒的,一旦发病,虾苗就相互残杀,一传十,十传百,几天过后,全池虾苗将荡然无存。大家查资料,想了不少办法,最后决定用猪骨头诱捕。于是,另外一位师弟飞身跃上自行车,一路狂奔,从农贸市场买回一头猪的全部骨头。放入虾池,结果效果甚微,只抓到几个,距几万只虾苗的目标可以说是千里之遥。我想到一个办法,向王兄汇报了,他也说可以一试,结果一举成功,很快完成此项任务。其实很简单,先通知养虾工停止投喂饲料,让虾苗饥肠辘辘;在池塘一角水底布上网,然后在网上投放饲料,可想而知,群虾毕至,满网而归。从那次起,这位王兄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,凡事与我商量。他年龄大,一些危险的或者耗体力的活,一般都是我抢着去干。我摇橹,他投饵料、测水质等。需要定期监测围隔底部状况的时候,都是我头朝下潜入水底,往往由于浮力潜不下去,王兄就抓住我的双腿往下按。我们形成了实验共同体,人字结构,相互支撑,配合十分默契。
当然也有不默契的时候,一次我们俩要回青岛向导师汇报工作,需要走三公里的小路才能到公路上搭乘公共汽车。这时,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来,拖拉机手认识我们,就让我们上车。我当时年轻,轻松飞身上车。王兄也学我飞身而上,只听嚓的一声,王兄忙叫到“坏了坏了,我的裤子开线了”。我一看他左腿裤腿成了裙子了,直接开档到底。我们只好让拖拉机手把我们送到镇上,他用手按住开线的左腿,一瘸一瘸地走进商店,买了五根别针别上,才算可以乘车回青。见导师时,他的双腿并得紧紧的,生怕导师发现,我在偷偷地笑。汇报完,他就匆匆离开,回公司了。当我第二天见到他时,他还是穿着那条别着别针的裤子,问他为何不换?答曰:一忙就忘了。
时光飞逝,如今我已经年逾半百,王兄和于兄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,最小的孔兄也四十好几了吧。由于同一师门,与王兄常常联络,但见面很少。我与于兄、孔兄一直没有联系,能不能联系上还是问题!谨以此文追忆一下我们的当年吧,那个艰苦而温馨、让人哭又让人笑的岁月。
我更相信我们真的有缘,让我们梦里相见吧!
2017年5月18日 四知堂